2018年,创业板某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由若干投资者认购,股份锁定期12个月。
作者:俞啸军
来源:金诚同达(ID:gh_116bfa8fc864)
一
上市公司定增的“保底保收益”
2018年,创业板某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由若干投资者认购,股份锁定期12个月。
在股份认购之时,有些投资者为避免投资风险,与上市公司的实控人签署了“保底保收益”协议,核心条款为:(1)在其认购的股份限售解除后,其抛售股份所得的净收益不低于认购股份的本金和固定年回报,若低于本金和固定年回报的,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实控人现金补偿。(2)在其认购的股份限售解除后,其抛售股份所得的净收益高于认购股份的本金和固定年回报的,超额部分由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实控人之间平均分配。
限售期满,上市公司股价已较认购股价下跌50%,投资者账面价值巨额浮亏,投资者对实控人提出差额补足的要求。现双方各执一词,或将诉诸法律,剑拔弩张。
二
对“保底保收益”法律关系的认识
现在,就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实控人在认购定增股份前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及其补充,让我们来剖析一下这个“保底保收益”,看看其中到底包括了哪些法律关系,这些法律关系究竟成立不成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果。
“保底保收益”是在投资者认购上市公司定增股票过程中协议产生的,投资标的是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实控人通过合意达成“保底保收益”的约定,由上市公司实控人负有一个单方允诺的或有之债,即上市公司实控人对定增投资者的差额补足承诺。
投资者认购上市公司定增股票,从程序要件上看,投资者的主体资格、报价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定增完成后,投资者成为上市公司股东,投资行为合法有效。
上市公司实控人同意对定增投资者差额补足,从形式要件上看,实控人是独立民事主体,具有完整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有权利按照意思自治原则为自己设定单方义务。
三
对“保底保收益”相关生效判例的解读
笔者搜索部分案涉上市公司定增保底保收益的案例,在已生效判决中,有一类的判决承认“保底保收益”约定的合法性,此类判决占多数。也有一类判决不承认“保底保收益”约定的合法性。
(一)承认“保底保收益”约定合法性的判决
1.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之间证券交易合同纠纷,2020年一审判决,(2019)鄂01民初8385号。
2. 上海小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清海证券交易合同纠纷,2019年一审判决,(2018)豫14民初403号。
3. 上海小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清海证券交易合同纠纷,2020年一审判决,(2019)豫14民初225号。
4. 舜耕天禾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2018年一审判决,(2018)川民初62号;2019年二审判决,(2019)最高法民终400号。
5. 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明朝勇证券交易合同纠纷,2016年一审判决,(2015)黔高民商初字第79号;2017年二审判决,(2017)最高法民终492号。
根据上述判决书记载,法院承认保底保收益约定效力的大体依据为:“保底保收益约定虽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但《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作为部门规章,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
(二)不承认“保底保收益”约定合法性的判决
1. 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与沈利祥合同纠纷,2014年一审判决,(2014)浙杭商初字第46号。
根据判决书记载,法院不承认保底保收益约定效力的依据为:“该承诺函的内容涉及操纵证券市场,扰乱证券市场秩序,侵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无效。”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承认或不承认“保底保收益”的案件,案情并非完全一致。在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与沈利祥合同纠纷一案中,有一节事实是原被告双方约定在某一特定时期持续买入“大东南”股票以维持股票价格构成操纵股价的行为,而其余案件未记载类似操纵股价的行为。所以,笔者理解,排除股价操纵情形外,其余上市公司定增的“保底保收益”案件均得到了法院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法理角度的判决承认。
四
泛滥的意思自治容易引起民法权利的异化
意思自治是民法基本原理,指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一切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变更和消灭,均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思,原则上国家不作干预。同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意思自治受到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的约束。
在不同的领域中,对公序良俗的理解和界定是存在差异的。《证券法》作为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的基础性规范,明确要求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由此可见,“三公”原则和“风险自担”原则就是证券发行、交易领域所应遵循的公序良俗。
定向增发是上市公司向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的形式发行股份的行为。其中,投资者有权根据自身的证券专业知识、财务水平和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判断,独立决定报价,独立决定认购股份数。此种情形下,在价格优先原则的指引下,没有与实控人达成协议的其他投资者,基于审慎原则,报价一般会较达成协议投资者偏低,认购成功率会相应降低。而已经和上市公司实控人达成了保底保收益协议的投资者,其报价自然更为激进,认购成功率也相应增加。
“保底保收益”的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实控人在矛盾爆发前,当事人不会透露该等秘密交易,也从未发生过主动对外透露该等秘密交易的情形。那么,参与定增的其他投资者、二级市场的股票参与者、证券监管机构等,更是无从获知。从这个角度看,“保底保收益”本质上是一场内幕交易,是协议各方对未来股价的一场合谋。“保底保收益”中的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是显而易见的。
投资者利用市场优势地位,规避了证券交易风险自担原则,将市场波动风险转嫁给上市公司实控人、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将定增异形为“明股实债”,是明显的市场风险错配,是典型的民事权利的异化。
五
守护公序良俗正是为了维护意思自治
纵观“保底保收益”已经披露的纠纷,笔者发现这一类纠纷多发生在民营上市公司之中,原因或许是不言而喻的。当民营上市公司实控人或控股股东同意“保底保收益”之时,大概率的情况是为了解决上市公司资金困境不得已而为之。虽与投资者之间有超额分配的约定,但作为上市公司的实控人,其自有股份已最大程度享受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和股价上涨带来的合法回报,其所谋求的超额分配,仅仅是利益均沾的小心思。无论是否出于自愿,“保底保收益”的核心困境终究还是陷于民营经济的融资难。业绩好、发展快、壁垒高、市场大的民营上市公司或许不需要类似“保底保收益”,但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讨论“保底保收益”,哪怕只有一家上市公司实控人提供这个承诺,就是为了减少和避免未来有更多的上市公司实控人限于融资困境而背负本应由投资者自己承担的投资风险。
在判断“保底保收益”是否合法有效,是否适用意思自治,笔者认为,不应该简单僵化的套用法条。譬如说,有的判决认为:“《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是2020年2月14日生效的,对之前的定增保底行为不具有溯及力。”譬如说,有的判决认为:“证监会的文件仅仅是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并基于这些条条框框,承认“保底保收益”的有效性,同时,会加上“意思自治”的民法原则,强化“保底保收益”的合法性。”此时此刻,如果站在狭隘理解的角度,这样的判定似乎是三段论的完美演绎,论据论点无懈可击。但是,当我们以更全面、更宏观的角度审视一下“意思自治”的合理边界,重温一下“公序良俗”本应有的价值取向,“公开、公平、公正”与“保底保收益”之间的公私利益冲突,就真成了真金白银的刺眼和不堪。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规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得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不得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在认定规章是否涉及公序良俗时,要在考察规范对象基础上,兼顾监管强度、交易安全保护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慎重考量,并在裁判文书中进行充分说理。
笔者由衷认为,判断“保底保收益”的合法有效性,更需要我们站在一个闪耀着理性光芒的高台上,秉持良善的价值观,审慎辨析。正如中国人大网2020年7月28日刊登的《更好守护公序良俗》一文所说:“人民法院只有准确适用民法典的公序良俗原则和相关条款,才能形成更多承载公平正义的判决。”
2023年7月22日-23日,诚邀您拨冗莅临。

拿包+尽调+处置+法拍+精华案例全解析!

做好不良资产,学这一门课就够了!

2位深耕该领域的大咖老师领衔主讲,用特殊机会投资视角拆解困境上市公司重组重整中的巨大机遇。

系统提升资产投资、经营、处置实操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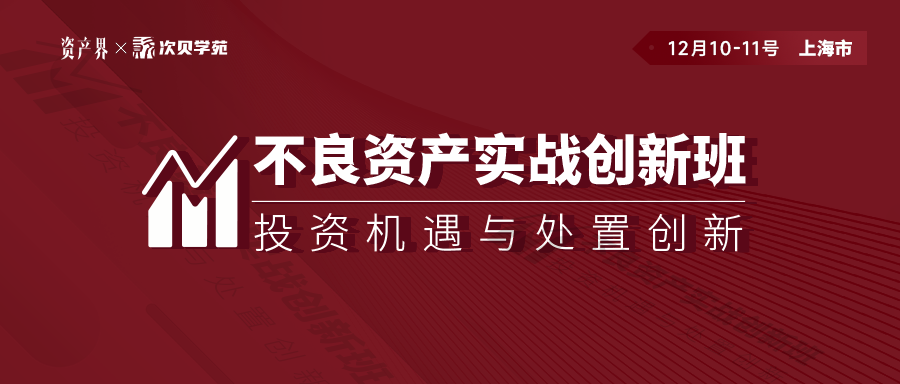
全面掌握最新结构化融资技能!


还没有评论,赶快来抢沙发吧~